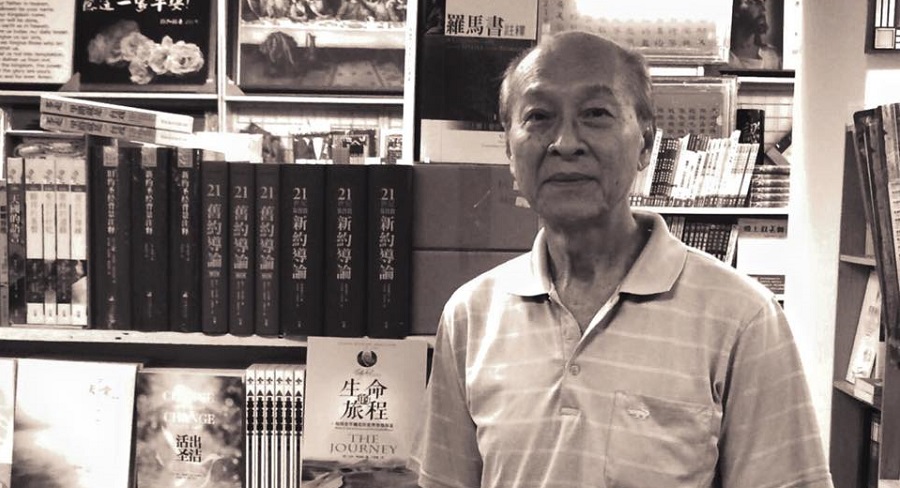文:張文光

(1) 在充滿傷痛、死亡、黑暗、苦難的世界,我們是否仍相信復活?
我們可有想過,世界上有那一個宗教,除了基督教,聲稱有一个人死了, 但又復活了;且仍然活在每个信徒的生命中?我們都尊敬歷史偉人,但我們不會說他們復活了,而且回到我們當中,甚至仍然管治支配我們的生活。但是基督教却信誓旦旦的宣告耶稣已经复活了,祂仍然與我們同行。基督徒每年都必定大事庆祝复活节。我們不可小看有復活節的這個事實。更不可忘记了基督复活以及一切相关的真理。
為甚麼基督徒竟然有絕對的勇氣說耶穌仍然活著?這是值得我們思想的。保羅在〈哥林多前书〉15章1节到2节如此说:“弟兄们,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接着保罗说了一番我们常在圣餐时所聽到的话:“我当日所领受有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這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福音。我們承襲了由使徒們所傳下來的信仰,所傳下來的福音。我們與使徒們,與世世代代的眾基督徒們,以及現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的基督徒們一起相信,耶穌復活了!我們有這樣的信心,因為我們已經傳承了這樣的信仰傳統。我們每週都會背誦《使徒信經》,內中有一個認信的宣告,“我信身體復活”。我們每個人都是屬於這個認信的群體。同時我相信我們也經歷了神仍然在我們的生命中活著。
但是我們也不必欺騙自己,有時神似乎離我們太遠了。我們似乎失去了復活的喜樂。我們似乎無法找到能領我們到這種復活的喜樂的途徑。
打開報紙,我們看到是死亡、罪案、暴力、恐怖襲擊事件,戰爭。而政治圈濫權、舞弊的事層出不窮,使我們不禁地大喊天理何在,甚至使我們懷疑神是否仍然存在。而在個人生命的層面,我們面對許多的壓力、失敗、沮喪,甚至傷痛。在充滿罪惡、傷痛、黑暗的世界,復活節的喜樂真的離我們太遠了。我們可能把復活節當作一個宗教的節日而己,表面我們慶祝復活節,但實際上,復活節在我們的生命中,可能毫無意義,也沒有任何影響。
(2) 如果基督沒有復活 (歌林多前书15:12-19)
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不要忘了“復活是基督教的內容與基礎”(神學家Karl Rahner之語)。如果基督沒有復活,就沒有基督教。保羅在林前15章開始的第3至4節說“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最重要的就是:照聖經所說,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和合本修訂版) 。接著保羅用了一共58節的篇幅來詳細討論復活的真理,為甚麼?因為當時也有人不再相信復活這回事。而且這些人不是教外的的人,而是哥林多教會裏的一群人!在12節保羅說:“既傳基督是從死裏復活了,怎麼在你們中間有人說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呢?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
保羅在12節到19節用很邏輯的方式推論出,復活的確實性 (Certainty),以及沒有復活的荒謬 (Absurdity)。
如果耶穌沒有復活,後果是嚴重的。17至19節列出這些後果:
“基督若沒有復活, 你们的信就是徒然, 你们仍活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
第14节也这么说:“基督若沒有復活, 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
甚麼是“枉然”?“枉然”就是“沒有用”;英文NIV圣經翻譯為useless。
不只是保羅所傳的是“枉然”的,哥林多教會的信徒所信的也是“枉然”,“沒有用”,“空”的。而且使徒也成了騙子,他們傳講謊言,為神作假見證,以神的名義說大話!
更嚴重的是,如果沒有復活,信徒們的罪就無法除去,洗淨,他們仍然在罪中。(〈歌林多前书〉15:17)否認復活等於否認他們已經接受罪的赦免。而那些死了的信徒,也滅亡了 (15:18)。信徒的盼望只能限制在今生,這比所有的人更可憐了 (15:19)。
(3) 但是,基督確實復活了 (林前15:20)
20節開宗明義的說:“但基督已經從死里復活…”。 和合本修訂版把它翻譯成:“其實基督已經從死人中復活….” 。NRSV聖經翻譯成 But in fact Christ has been raised from the dead。NIV 版圣經更加清楚的說:But Christ has indeed been raised from the dead。耶穌復活是一個事實, 一個歷史的事實。
保羅接着解釋說,這事實上已經復活的基督,是“初熟的果子”(first fruits)。
各位如果有種菓樹的經驗,就知道如果菓樹中有一粒菓子熟了,接著下來, 所有的菓子必定按它們的時間而熟。我的父親有一塊榴連園,每當榴連季節到來,榴連成熟時,我們就得幫忙拾榴連。榴連成熟了,就會自動掉下來。而且好象晚上掉的機率比較高。我們必須在晚間拿着手電筒走遍榴連園到處找榴連,拾榴連。第一粒榴連熟了,噗咚的掉下來,其他在樹上的榴連肯定會按它們的時間掉下來。絕對不會有一粒不熟的榴連,一直青青地掛在樹上,留到下一季。家中有種過芒菓樹的弟兄姐妹,大概也能了解這個道理。
這裡保羅所強調的是復活的肯定性。我們這群相信主,已經“睡了的人”必定復活。為什么,因為基督已經先我們復活,他的復活是一種保證, 一種Guarantee,是一種訂金, Down-payment。信徒復活是一定會發生,無可避免的。
保羅不用“死了的人”這個詞匯, 而是用“睡了的人”,因為睡著的人一定會醒過來。
(4) 在基督裏,眾人都要復活 (林前15:11-22)
保羅在這裡第一次用到“亞當與基督的類比” (Adam-Christ Analogy),另外一處是在第45至49節以及〈羅馬書〉5章12至21節 (參Gordon Fee对〈歌林多前书〉的解經書 (NICNT 系列,頁750) 。
基督代表新人,新秩序 (New Order);而亞當代表舊人,舊秩序 (Old Order)。
因為亞當犯罪,罪入了世界,死也接著而來,但藉著基督的復活,在基督裏的人,也要復活。記得,這裡說是“在基督“裏的人,即相信基督的人。保羅沒有在這裡提倡普救論。
基督從死里復活的意義何在?意義重大無比。〈希伯來書〉2章14節說,基督成了血肉之體,特要借着死,敗壞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釋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為奴仆的人。這里雖然沒有說到復活,但是我們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但第三天后,他復活了。神借着耶穌的死亡與復活,擊敗了罪惡死亡。
我們這些相信基督的人,已經與祂復活的生命連接了,因此我們有永生 (Eternal Life)。 我們的生命因而有終極的意義 (Final Significance),有永恆的價值 (Eternal Worth)。我們不相信人死如燈滅,死了一了百了,我們的一生歸於無有,歸于無意義。相反的,我們深信,如果我們與基督同死,也必定與他同活 (參〈羅馬書 6:4-11)。
(5) 復活真理的現世意義
5.1 復活是在受難之後
我們可能正面臨許多的痛苦、甚至死亡的威脅。親人的病痛可能使我們毫無喜樂。但是我們必須記住了,復活節的光輝是為了那些接納且自願忍受到底那受難節之黑暗的人而發出的(神學家Karl Rahner之語,原文為:the light of Easter shines only for the ones who have accepted and voluntarily endured to the end the darkness of Good Friday)。
我們不需要否認我們的痛苦,回避我們的傷痛。我們不需要逃避受難節的黑暗。但在黑暗之中,我們必須學習忍耐到底。
保羅在〈提摩太後書〉2章11至13節教導我們說:“有可信的話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祂同活;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祂一同作王。”
保羅說也說:“我想現在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羅馬書〉 8:18)
我們必須再次認信,祂仍然活著,祂已經勝過罪與死亡。他曾經墮落罪惡與死亡的深淵,但是在第一個復活日,他已經從這個深淵崛起,進而升天了。然而祂不是從此“隱退江湖”,不問世事,相反的,祂仍然眷顧我們,現在上帝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參羅馬書8:34)。
5.2 如何重拾復活節之盼望與喜樂:與主聯合依靠他
靈修大師,也是暢銷書Divine Conspiracy 的作者,巍樂德(Dallas Willard)說過:希望是期待尚未來到的事情,或未看到的事情(參希伯來書11:1)。中國人喜歡說:“好事近”;我想,我們基督徒的“終末盼望”(Eschatological hope),基本上就是一種堅信“好事近”的現世生活態度。不只是好事近,我們進一步深信,因為基督的復活,好事已經開始了。接踵而來的,會有更好的事發生。復活的耶穌開啟了一個新的秩序,一個神的國度,啟動了一連串新的、好的事情;無人可以阻止。而這些好事的最終高潮,就是我們身體的復活,與神在一起,包括統治這個世界。
然而在這段已濟與未濟(already but not yet)的期間,我們必須耐心等待。羅馬書8章24節說的好“我們得救是在於盼望;可是看得見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誰還去盼望他所看得見的呢? 但我們盼望那看不見的,我們就耐心等候。”而12章12節列出一個面對苦難,黑暗日子的秘方:“在盼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希望我們能將這秘方緊記于心。
耶穌在被釘受難之前,向門徒說了一大段的話,記載在〈約翰福音〉第13章至至17章,其中真葡萄樹與枝子的說話佔了甚大的篇幅 (15:1-11)。耶穌教誨門徒們必須常與真葡萄樹 (就是基督) 聯合,不斷汲取生命的養份, 從而多結果子。過後主耶穌在11節總結真葡萄樹的教導說:“我已對你們說了這些事,是讓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裡,並讓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新譯本作“滿溢”,NRSV 作 So that your joy may be complete)。
我們必須記得,喜樂的源頭是主,我們必須恒常與他聯合。如果我們生命枯萎,大有可能是因為我們已經脫離真葡萄樹。更糟糠的,我們的生活可能充滿罪惡,使神掩面不看我們。我們必須坐言起行,馬上尋求重新與神圣的主聯結。
無可否認,喜樂是聖靈的果子,但是我們不可以什么也不作,等上帝使我們喜樂起來; 換句話說我們不可消極與被動。巍樂德(Dallas Willard) 說如果我們要獲得喜樂,我們不可一味回顧過去的罪與失敗,或向前看前面所會發生的事,或向內看我們的欠缺,或我們與工作、責任、試探的掙扎等,而使這份喜樂消耗了。如果我們這樣作的話,我們是把盼望錯放在我們自己身上。我們無須這樣作,反之,我們應該望向神的偉大及良善,以及祂在我們生命所成就的一切。
5.3 不可動搖,竭力多作主工 (林前15:58)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15章這一章討論復活的篇章里,以勉勵當代的信徒不可動搖, 要竭力多作主工作為結束。英文《圣經》NRSV版本的翻譯非常好:“Be steadfast, always excelling in the work of the Lord”。其中帶出不只是竭力作主工,而且要作的卓越。
保羅勸勉當時的信徒不要被那些提倡沒有復活的人或思想所影響,相反的必須忠於當初所領受的福音;要緊持信仰的根基,信仰穩固,不要輕易被迷惑而偏離正道。信徒的基本態度必須是不輕易被改變,不偏離福音的盼望 (林前1:23)。 如果神已經使基督復活了,勝過死亡、罪的權勢,那我們所做不會是空幻,徒然的 (Not in vain) (15:1-2)。
讓我們每一次慶祝復活節的時候,重拾復活節的盼望與喜樂。也再次重新立志,為了所領受的福音真理,獻上我們的青春與力量,因為我們深信這些努力不是白費的;而切切相反,我們為神所作的都是有永恒價值的。
[注: 这是一篇讲章,讲于2008年复活节期间。所引用的經文是新约〈哥林多前書〉15章第20至28节]
 《圣经》 〈传道书〉的作者也如此教诲: “光是甜美的,眼见日光是多么好啊!人活多少年,就当快乐多少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必多,所要来临的全是虚空……”。既然是“虚空”,那还需要认真吗? 游戏人间就就好了。奇怪的是,没有,传道者没有这样劝导我们。反而急不及待地补充说:“年轻人哪,你在少年时当快乐;在年轻时使你的心欢畅,做你心所愿做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神必审问你。”又说了那句重话:“这些事都已听见了,结论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事恶,神都必审问。”
《圣经》 〈传道书〉的作者也如此教诲: “光是甜美的,眼见日光是多么好啊!人活多少年,就当快乐多少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日子必多,所要来临的全是虚空……”。既然是“虚空”,那还需要认真吗? 游戏人间就就好了。奇怪的是,没有,传道者没有这样劝导我们。反而急不及待地补充说:“年轻人哪,你在少年时当快乐;在年轻时使你的心欢畅,做你心所愿做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神必审问你。”又说了那句重话:“这些事都已听见了,结论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事恶,神都必审问。” 莫内尝试捕捉那千变万化的浮光;世人也竭力在流动的光影中,捕捉那稍纵即逝的片刻。有者则提倡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尽力把自己一生以最美丽最璀璨的方式呈现一番就好了。我们尝试在自己充满挑战、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一些能克制“短暂”这个死敌的东西。但往往我们都忘了,我们的种种努力,最终是不完全,甚至是支离破碎的。在传道者发出他的智慧箴言约300年后,巴勒斯坦加利利那位最大的智者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
莫内尝试捕捉那千变万化的浮光;世人也竭力在流动的光影中,捕捉那稍纵即逝的片刻。有者则提倡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尽力把自己一生以最美丽最璀璨的方式呈现一番就好了。我们尝试在自己充满挑战、有限的生命中,创造出一些能克制“短暂”这个死敌的东西。但往往我们都忘了,我们的种种努力,最终是不完全,甚至是支离破碎的。在传道者发出他的智慧箴言约300年后,巴勒斯坦加利利那位最大的智者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